我是1939年生人,家在河北沧州泊头的齐桥镇。我家里有兄弟四个,我是老大,下面还有一个妹妹。现在有个弟弟在老家,另外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在新疆。
我家是农村的,种地,家里条件穷得要命,太穷了,我小时候印象都不深了。我记得我上了几年学,小学毕业以后没法再上了,就在家待着。村里开始叫互助组,后来是合作社,就是吃大锅饭,都有吃的。但是吃着吃着就没有粮了,后面就又是饿肚子的日子。我是家里老大,就得想办法挣钱。
到了17岁的时候,兰州铁路工程局到我们那招工,临时工,说是去修兰新线。我都不知道兰新线在哪儿,怎么修铁路也没概念,但是能挣钱啊,就报名了。我身体不好,跟着施工队去兰新线的银)I段,干了一年半。所谓修铁路,我们的活主要是拾石头。我身体挺弱,一是干不动,一是太艰苦,三是刚离开家,总想家。工地里大点的人都开玩笑,说河北来的小鬼还哭
鼻子呢。说就说吧,我才17周岁,搁现在也就上高二吧。
我们白天修路,晚上住在帐篷里,吃饭都是从兰州运来的粮食。吃完了饭,喝点水,碗底下都有沙子。太苦了,荒郊野岭,那个风太冷了,不是一般的冷,帐篷里都冻透了。修铁路得先修公路,再修铁路,因为修路的人得吃饭喝水啊,修公路是为了能运粮食和材料。我们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那段修公路,全都是沙子,根本没法修,后来是把一段土长城给平了,因为就那一段还能平出来,就在长城上修的公路。
累是累吧,但是有工钱,还不少,一个月42.5兀,我每个月给家里寄30块钱,我家里在村里就算富裕了。这么干了一年半,太累,身体也不行,总觉得胸口疼,他们就说你别干了,我也怕再得上什么病,就回来了。
我被安排到了一个民兵营,我会吹号,就让我吹号,也不干别的,就只管吹号。
在民兵营待了几个月,我们公社有个张书记,不知道从哪儿知道我的,有一天派人找我,让我去他那干,说缺个人。后来我知道了,实际上就是书记的通信员,跑跑腿,发发通知什么的,不过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啊,让干就干吧。
刚去了就赶上任务,张书记找我,说有一个村没粮食吃了,让我去另一个村喊支书,让那个村的支书给他们送粮食。张书记问我,这事儿你听明白了吗?我说明白了,书记说,那你去吧。
我记得是晚上跟我说的,那书记让去了还敢不去?赶紧骑着自行车走,一晚上跑了两个村。农村哪有路啊,俩村还挺远,我摸黑骑了一晚上,才把事儿办完。回来时书记问我,通知到了吗,我说都办妥了,他还挺满意。那以后他对我就都不错。
1958年底,外地就有接兵的来了,我正好是在年龄,书记说红恩你当兵去吧,我说行。给我定的是去延庆当汽车兵,我觉得能开汽车了,也挺高兴。到了体检出了点岔子,按照标准,我还差点份量,吃不饱啊,太瘦了。书记又找人给说了说,人家就同意我去了。
等还差一天就要走了时,他们说天津公安局也来招人了。后来张书记又找我,说你甭去了,你去天津当警察去吧。我说不合适吧,延庆的都定好了。他说没事,我帮你找他们解释,他说当警察是一辈子的事儿,当汽车兵不定哪天回来呢。
说起来也有意思,打从我说要去延庆当汽车兵起,我娘就在家里又哭又闹的,非不让我走。可是等着一听说我不去当兵改当警察去了,也不哭了也不闹了,还挺高兴。她可能是旧思维,以为当兵就要去打仗呢。
当时知道是来当消防警察。我们有一个政委王陆海,他带队去的。还有一个刘桂荣,是他去民兵营找的我,我还带他办过一些事儿。他后来在公安学校当队长,后来公安学校毕业了,我说我去哪儿呢,他说你跟我走吧。
刘桂荣是11队的队长,我就跟他去了11队,去当战斗员。我在班里是6号,离火比较远,主要负责领路。干6号得熟悉街道,领着车走,说白了就是得找到火场在哪儿。你还得知道消防栓在哪儿,得找到水。进了火场我就是通信员,得负责下达现场指挥的通知,还负责两边的联络。
在这没俩月,消防这块又新建了个中队,是杨庄子中队,我又分到杨庄子中队当了电话员,负责接报火警。又是个得动脑子的活,这和6号一样,得记性好,机灵,知道怎么分析情况,反应也得快。我干电话员干了3年,也不光是在办公室里接电话,我们有句话叫"有事办公安,无事搞生产。1960年得去干活。干这个累,也没有额外补贴,就是响应号召。我记得工资刚来是17兀,后来34.5兀,到了1960年就有40.5兀,我领这个钱一直到我下放。
我是1961年结婚的,对象是我老乡,在老家当老师。我俩是一个村的,我来天津之前婚事就定了。我们是在天津结的婚。结婚太简单了,我对象背了个被子就来了,没有摆喜酒也没有仪式,就是叫同事在一块宣布了一下,我俩给大家举了个躬,就算是结婚了。当然也领证了。我们结婚一共干了这么几件事儿:一个是我们租了个旅馆住了几天,给老家买了一些糖和点心,再买点生活用品,对了,还买了一件棉袄,大概一共花了150块钱,就没了。回了趟老家,发了些糖,也没办,也是没钱办。
结完婚她就回去了,我们一直两地分居,我一年就回家一次,待半个月,也不闲着,农活也都得帮着干。
到了1970年,天津新建了不少学校,需要小学老师,我那时候已经在政治处了,了解到这个信息,就帮着把老婆调过来了,当老师。来了总得有住的地方吧,公安招待所给我调了一个9平米的小屋,我俩结婚第十年,好歹是住一块了。住了多半年,有个军代表回老家了,他的房子闲下来,他们就给我倒了了一下,说,你去住吧。我就搬到了16平米的大屋。这是个筒子楼,虽然做饭在楼道,共用公共厕所,生活环境和现在比差远了,但是那时候刚从小屋搬过来,觉得大屋太豁亮了,太舒服了。
后来赶上地震,我们就住消防队里,一直到1989年才分的房子,也就是现在住的房子。
1963年,机关上搞三五反,人不够用,我就到机关来帮忙。那时候叫政办室,就是政治办公室。我还负责外调,总出去,都骑自行车去,去霸县都是骑自行车去。这都不算啥,后来到宝坻去外调,自行车不够,我还做。一等"啊。什么是。一等。?就是自行车后座,坐坐你就知道了,还不如骑着舒服。
1965年5月1日消防民警转现役,第一批兵招的就是河北卢龙的。新兵来我当时字写得还行,让我负责抄下来,那真是没白没黑地抄。夏天,屋里太热了,就上院里抄,蚊子咬好多包。
后来我就调到政治处了,就开始管干部。去政治处是高恭敏推荐的我,我算干事,负责审干、外调、考察干部这些事情,基本上是都忙活。我干的都是具体的事儿,特别细小特别麻烦的事儿,这些事儿领导还都比较放心交给我。有时候我也分析,我一没本事,二没学历,三没口才,领导为嘛还喜欢我呢?后来我觉得可能是我有点"鬼道。。。鬼道。是我老家话,就是机灵的意思。我觉得我还有一点,就是踏下心干事儿,少说漂亮话,咱没啥大本事,但是能做这些具体的事儿。
我管干部管的多,到了文化大革命,造反派让我交代领导干部的情况,其实就是揭发他们。我什么都没说,我说档案里都有,你们自己看去,其他的我都不知道。后来军代表来问我,让我说说干部们有什么特点,我这才说了说,当然谁的坏话也没说。
1969年。砸烂公检法。,公安这块全体下放,我分到了盐厂,在汉沽,属于劳改一队。他们把犯人调走了,然后把公检法的人调过去当劳动力,我就在这个队里。到了1970年,又重新分配,我又去天津化工厂,后来我又到了矿山电气。后来有个17次公安会议,总理讲了,全国公安要调回一部分老同志,总得有人干事儿啊,陆陆续续有些同志就回来了。杨春峰也回来了,当时军代表掌权,问他,有没有能管干部的,就把我想起来了,让我回来继续干。就这么的,1972年底让我办完手续,1973年初我回到政治处。
我在政治处是抱着这么一个想法,当干部的事情对个人都是大事儿,无论是提拔还是考察,这事儿都是凭良心干。队伍建设需要干部,错了不行,但是不当回事更不行。好多兵都从农村来的,提了就能留城市了,他们也希望尽快脱离农村。我去考察,给领导汇报,领导说行,一般就行了。都不容易,要是当了干部就能留在城领导采纳了。
我记得还有这么个插曲。
宝坻有一个刘奎,是个不错的班长,身体素质很好,他们那一祛赶上提干,选的干部都是班长出身,都是干出来的。但是要考试,有文化课和理论考试,考试的时候他不会啊。后来他在考试卷上写诗,我还记得。回想昔日练兵场,龙腾虎跃露锋芒,拿起三寸鸡毛笔,心情激动似断肠。。我一看,这行啊,我马上找领导,我说他虽然没答题,但是有点歪才,而且业务很好,能不能破格。结果他就过了,后来提的排长。当时还有一个2队的杨国龙,挂钩梯是一绝,也是我提的。
还有一块是考学。我记得有一个叫王宝军的,他是我们的战士,个人条件不错。那时候赶上夏县武警专科学校招人,得查体,当兵的时候查的他身高是170mm,后来可能大夫有点忙,一查169mm,警校不让进,差一毫米。这可急坏了,我赶紧找人,我说我们是尺子量的,量的时候没问题,可不能卡在这一毫米上啊。他自己也念叨,当了两年兵抽抽了(笑)。后来是让他上了,上完回来就提干了。
还有一个也是夏县来招人,我们推荐了个叫刘继国的,也是体检的问题,他眼有问题。我说这得想想办法,我就跟政治部说,眼差点,咱跟公安医院说说,要不太可惜了。最后这个也算是特批了。
我老是从这个角度来想这些人,得会说,知道他有如心里想什么。比如有的当兵5年没提干,该复原了,闹情绪不走,也经常得是我去安抚。还有一次我记得挺清楚的,有一个干部犯了点错误,已经提了排长,组织研究决定除名吧。当时我们下面叫片儿的,片儿长就弄不了这个事儿,太简单粗暴,说说就顶了,他就是不走。后来让我去,我就说前面的事儿咱都不提了,你回去好好干,回农村就好好干,他都答应了,回头又被片儿长数落两句,又不走了。这么闹了好几次,后来到底是走了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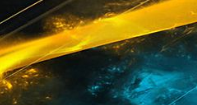

评论列表